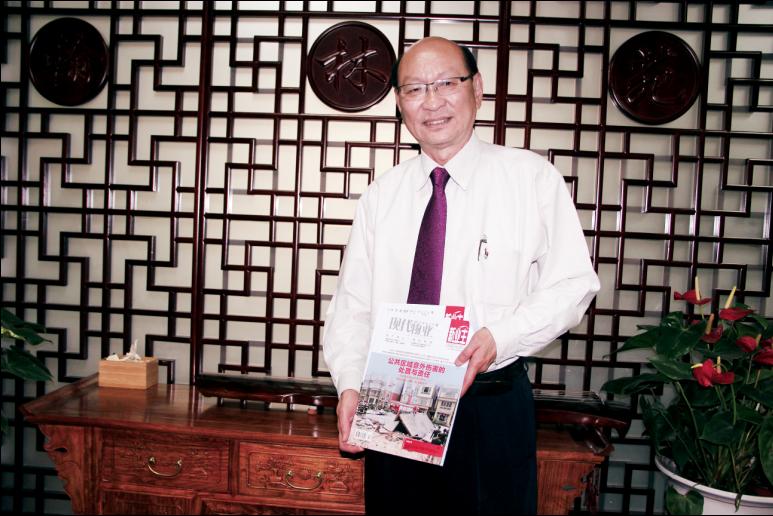 柯木林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成立于1960年,由其承建的公共住宅容纳了约 83%新加坡的人口。除建设外,建屋发展局还组建物业公司管理住宅。新加坡怡安产业公司即其子公司,为约60%的公共住宅提供物业管理。怡安产业原中国部总裁柯木林认为,新加坡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健康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
柯木林,曾供职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新加坡怡安产业公司原中国部总裁,现为清华大学物业资产管理高级研修班顾问,《物业管理运作指南》主编。拥有超过40年的物业管理从业经验,并将新加坡物业管理经验传入中国。
《现代物业》:您在1994年的时候就将新加坡的一些实践经验引入中国,当时中国物业管理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柯木林:新加坡的物业管理起步相当早,从英国殖民地时代就出现了所谓的“信托局”住宅。比较系统地实施物业管理是从1960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成立时开始。我是在1972年进入物业管理的工作。1994年我来到中国时,距离我入行已经有22年的时间。当时我的感觉是,中国的物业管理处于混沌的状态。话虽如此,但广东深圳等地方已出现物业管理的种子。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厦门的物业管理不如上海。由于我们是较早过来中国发展的物业公司,当时给人一种生意很容易做的感觉,你不用找项目,项目来找你。我在中国做了不少物业管理培训,让同行了解物业管理是什么。
我来中国时,在新加坡已有20多年的物业管理经验。那时,新加坡的物业管理已有很多标准,我们只要根据这些标准做就可以。但来到中国后,这里的市场逼着我思考和静下心来把物业管理的理论理顺,因为不断有人会问“什么是物业管理”。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摸索,我把物业管理总结成了八个字,“一项服务,四种管理”。所谓“一项服务”,指的是客户服务;“四种管理”为维修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法纪管理。物业管理是个系统工程,这八个字既容易让人记住,又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理论书籍时有个头绪。我在许多地方讲课时也经常提这观点,了解这八个字做物业管理就容易了。先把大纲弄清楚,再去谈细节的东西。
当时我们做住宅物业管理的项目比较多,但我发现小区管理比较繁杂。原因是我们面对的群众对物业管理的认识程度不足,他们以为物业管理只是扫地看门,很多复杂的理论和知识并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评价标准就是地不干净、大门没有管好等,而且动不动就以吵架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大多数时间都在应付这些琐碎的事。
后来中国的物业市场取得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很多高端的物业公司。这个时候由于市场肥了,大家都来抢,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也越乱,现在的物业管理市场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写书的人不一定有实战经验,有实战经验的不一定会写书。我所著的这本《物业管理运作指南》(2000年6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12年10月再版)就相当于一本菜谱。这是根据我的实战经验写出来,你根据这个“菜谱”来做,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你已经有了一个起步。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供职的公司并不赞成,他们认为这是把自己吃饭的本钱公开了。但我认为只有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别人才能知道你有多好,就像每个看了名厨师写的烹饪手册,不一定都能成为名厨。
《现代物业》:新加坡的物业管理公司为公共住宅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柯木林:我们的服务是以“物”为主。以“物”为主是指确保房子硬件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能够做得好:例如电梯、水泵坏了有高效的修理,并且24小时在岗服务,与业主的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少,吵架的事情也少。
在中国,物业管理和业主的争吵较多,我认为在中国既要管理好“物”,又要服务好“人”。我们既然是一个服务行业,就要让业主对自己产生好感,才会愿意进一步交谈。所以当时公司就雇佣了许多美女帅哥,这是借鉴酒店的管理经验。但形象工程做到位以后,服务必须要有内涵,单靠一张漂亮脸蛋是没有用的。当雇佣到理想的员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充实他们的专业知识。服务方面不能忽悠业主。当时的培训工作主要由我负责,由我和新加坡派过来的同事培训一批人,再由这批人培训下属。
我常常举例说,刘邦打天下才三个人——韩信、萧何、张良。我们只需要培养一批骨干就可以,不需要太多人。我们当时就培养了五个人,我们称他们“五虎将”,谈生意时这五个人都能有很大的收获。现在这五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错的表现,其中一个在广西的开发商当老总,一个在上海的物业公司做总经理助理,还有一个在新加坡。
好的物业公司能使物业保值、增值。保安、前台、绿地、清洁都是门面,第一眼给人的形象是一本公开的成绩册,但要做好却有一定难度。
(未完)
(责任编辑:现代物业)《现代物业•新业主》2014年第6期/总第292期 |

